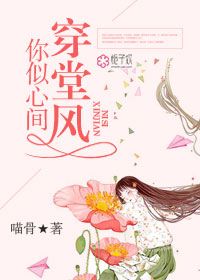随着勘查的深入,天色愈发黑暗。小孙打开便携式紫外线灯,在地面和植被上照射,希望能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痕迹。突然,他的灯光停在一片草丛上,几片叶子上泛着淡淡的荧光,“荧光反应,可能是血迹。”他用棉签小心擦拭,装进证物管,“得带回去做鲁米诺检测确认。”
在对周围树木的检查中,小杨发现一棵松树的树干上有几道平行的划痕,间距与小孙之前在岩壁上发现的相似。“这痕迹像是刀具或金属物品划出来的,”他拿出物证标签,“而且位置高度在1米7左右,符合成年人抬手的高度。”然而,当他们试图寻找更多关联线索时,却一无所获。
整整六个小时过去,山间的雾气愈发浓重。小杨和小孙将收集到的物证一一登记,疲惫地回到崖顶。“虽然发现了不少东西,但都还不足以锁定凶手。”小孙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“血迹、足迹、随身物品...都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对。”小杨点头,看着远处闪烁的警灯:“至少我们知道这不是意外,凶手就在暗处。”
李明接过两人的勘查记录,翻看着密密麻麻的笔记和照片,眉头紧锁。这场看似普通的坠崖事件,在抽丝剥茧的勘查后,显露出复杂的谋杀真相,而那些收集到的线索,如同散落的拼图,等待着后续更深入的调查与分析,才能拼凑出完整的画面。
与此同时,小王这边也在了解相关的情况。警车的应急灯在暮色中明明灭灭,将小王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。他蹲在两个报案的驴友面前,笔记本摊在膝盖上,笔尖悬在纸面迟迟未落——面前的年轻人还在因为惊吓而语无伦次,冲锋衣上的泥浆混着雨水,在草地上洇出深色的痕迹。
“别急,慢慢说。”小王递过去两瓶温水,瓶盖拧开时发出轻微的“啵”声。戴眼镜的男生叫陈默,是某大学地质系的学生,另一个扎马尾的女生是他的同学林溪,两人趁着周末来爬野山,没想到撞见这桩凶案。
陈默捧着水杯的手还在抖,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:“我们本来走的是常规路线,下午三点左右,林溪说想抄近路看日落,就拐进了这条岔道。”他的声音突然拔高,又猛地压低,“大概五点半吧,听见悬崖那边传来‘砰’的一声闷响,像是什么重物砸在树上。”
林溪接过话头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冲锋衣的拉链:“我们以为是石头滚落,没太在意。可走了没几步,陈默用望远镜往后看,突然就僵住了。”她打了个寒颤,马尾辫上的草屑簌簌掉落,“他说...他说好像看到树杈上挂着个人,我不信,抢过望远镜一看——”女生突然捂住嘴,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,“那人脸朝下,胳膊垂着,血顺着树干往下滴,把下面的石头都染红了。”
小王的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:“你们听到声响时,周围有没有其他人?比如说话声、脚步声,或者其他动静?”
陈默努力回忆,眉头拧成疙瘩:“风声很大,还有鸟叫...好像...好像听到过几句争吵,但离得太远,听不清内容。当时以为是别的驴友在吵架,没往心里去。”他突然拍了下大腿,“对了!我们拐进岔道时,在路口看到过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,背着很大的登山包,往悬崖方向走。当时觉得奇怪,那条路根本不通往任何观景台。”
“能描述一下那个男人的特征吗?”小王追问,笔尖在纸上顿住。
林溪咬着嘴唇思考:“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左右,中等身材,头发很短,走路有点外八字。”她突然想起什么,“他左手手腕上戴着块很大的手表,金属表带,阳光下反光很厉害。我们跟他擦肩而过时,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汽油味,特别浓。”
陈默补充道:“他背包侧面好像露出来一截黑色的东西,看着像...像刀柄?当时没多想,现在想来太吓人了。”他的声音发颤,“我们发现尸体后就赶紧报警了,不敢靠近,一直在上面等着。期间没看到任何人离开,那条岔道是单行道,除非他从别的地方下山了。”
小王让两人辨认现场照片,当翻到死者的登山靴时,陈默突然指着鞋跟:“这种Vibram大底的登山靴,我们系里很多人穿,但他这款鞋跟处有个特殊的磨损痕迹——像是经常用鞋跟磕石头。刚才那个黑夹克男人的鞋子,好像也有类似的磨损。”
林溪却摇了摇头:“不对,死者穿的是蓝色冲锋衣,而那个男人穿的是黑色夹克,颜色对不上。”她突然指向照片里死者紧握的右手,“他手里攥着的是不是登山绳?我们看到的那个男人背包上,确实挂着一卷橙色的登山绳,颜色一模一样。”
询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,天色彻底暗了下来。小王合上笔记本,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线索:黑色夹克、汽油味、金属手表、可疑背包、特殊磨损的登山靴...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,拼凑不出完整的画像。两个年轻人提供的细节看似重要,却缺乏决定性的指向——那个神秘男人可能是凶手,也可能只是恰好路过的驴友。
警车的引擎重新启动时,林溪突然敲了敲车窗:“警察同志,我们刚才在岔路口捡到这个。”她递过来一枚银色的纽扣,边缘有细小的缺口,“当时以为是普通垃圾,现在想想,说不定是那个男人掉的。”